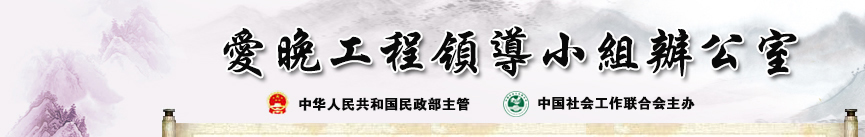卡夫丁峡谷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城附近,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团,并侮辱性地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从此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马克思在谈到有关俄国革命时曾提出过俄国革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它的内容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充分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本文将“卡夫丁峡谷”这个概念借用来喻指人口老龄化阶段,并研究认为,中国选择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无可规避地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结局,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必须通过的一条“卡夫丁峡谷”,要从容应对。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在1877-1882年间研究和回答作为封建专制的沙皇俄国能否通过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而提出来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意即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等东方国家果然做到了这一点。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状态,按经验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负作用,所以,笔者对人口老龄化也视作“卡夫丁峡谷”。
如约而至: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性
人口老龄化,通常是指,在一个人口总体中,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老化标准: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或者说,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我认为这是势所必然不可避免的。
中国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化。20世纪70年代初,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于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急刹车”式地控制人口增长,首推“晚、稀、少”生育政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并一以贯之坚持不懈。至今30多年来,中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口。其间生育水平(TFR)已从1971年的5.44下降到目前的更替水平(2.1)以下(确切地说,已下降到1.8以下)。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了变化。
试想,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增长而保持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变,那么中国目前至少是16亿人口,往后还要增长多少亿人口不可预料。如此而已,其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就目前13亿人口的状况而言,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选择了控制人口增长就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结局,无可规避。
社会进步促使人平寿限延长,而人平寿限延长又推助了老年人口规模膨胀,以及与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社会长期战乱、动乱的局面,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使得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包括老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往后生产进步,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享受的福祉越来越多(包括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于是全社会人平寿命不断延长:1949年的40余岁一直上升到目前的70多岁。死亡率下降和人平寿限延长从一个方面推助人口膨胀,包括老年人口规模膨胀。从“一普”到“五普”,我国60岁及上人口分别是,1953年为4154万,1964年为4225万,1982年为7664万,1990年为9697万,2000年为1.3亿。21世纪上半叶,由于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实施,人的平寿限有望再延长,我国老年人口将加速增长(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年增长率已是出生率的3倍),因此,未来三、四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还将突破2亿、3亿、4亿,老年人口的份额最终将占到1/4,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而且高龄化趋势明显。这都是空前的历史性的。这种状况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反言之,社会进步不致如此那是不可能的。
通过“卡夫丁峡谷”前的心理预约:平静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世界为伴。世界人口增长史表明,20世纪是世界人口暴增的世纪:从世纪初的16亿增长到世纪末的61亿。该世纪连续突破了第二、三、四、五、六个10亿,新增人口约占61亿人口的74%。而且,10亿与10亿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以至于50亿人口增至60亿人口只用了12年时间(1987—1999)。这的确是一种“爆炸性”增长趋势(资料来源:乔晓春等编著《人口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同时起步:从1650年清初的5000万人口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口,300年间增长了26倍(而世界只增长了6倍)。若以1950年为起点作比较,中国与世界增速相同:都约为2.4倍。虽然中国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搞“急刹车”式的控制人口增长,人口转变快,人口老化也快,但总起来是“老龄化世界中的老龄化中国”:未来中国老年人口达25%,预计世界也在21%(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2002)。按照邬沧萍教授的研究,未来中国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并非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29.3%、21.7%,仍低于发达地区的33.5%、26.8%,远远低于日本的42.35%、36.4%,也低于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国家。
从中国人口“老”化实际出发考察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没啥不得了。首先,虽然2000年起中国步入了年老型人口结构阶段,但不等于到60岁的人都老了。我们知道,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起始年龄,这一标准是1980年代初联合国在其1956年规定65岁作为老年人起始年龄基础上又添加的一个标准,这种作法明显有悖于实践,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我们都承认,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同龄人相比,都显得健康年轻和有用。笔者作为50多岁的见证人之一,凭证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50多岁已成佝偻老人者随处可见(我的祖母象我这般年纪已经病弱过世),而如今70多岁仍思维敏捷健步如飞者比比皆是。所以我认为,“水涨船高”,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平寿限的再延长,60岁成为中年年龄的年代已经到来(就中国和发达国家而言)。由此看来,60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的作法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可喜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60岁划为中年年龄段)。其二,要注意到中国的“人造老化”现象。中国由于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实践正在与理论“二律背反”:事实上不仅限于60岁及以上的人口老了,还有,从养育角度而言,目前全社会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费者已在2200万人以上,加上吃失业保险金者,加上40多岁、50多岁“内退”者(还有原来30多岁“病退”的),加上我们的社会讲究“年轻化”致极,许多单位用人是超过35岁者不要(这种搞法,无疑使35岁以上者都“老”了);此外,眼下党和政府又在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救助活动,这使得社会上被养育的人群还在扩大。这些说明,我们“养老”早已不仅限于60岁及以上者了,而是一种“既养老又养小还要养少”局面。其三,应解放思想,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人口老龄化不好,有负面效应,一般是,增加抚养负担,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使社会有可能显得保守、沉闷、缺少活力等。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人口老龄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效应。从实际看,主要有:一是,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有价值的劳动力资源增值。我们知道,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成材成器需得几十年的“磨合”。日本人将人的老年阶段称作“熟年”,可想而知,这个“熟年”的延长无疑是有价值的劳动力资源自然增值,同时也使得社会培养新增劳动力成本减少或下降。这未必不是好事。二是,意味着一个成熟社会的到来。一个社会老成持重者增多,加之就业率提高,将使那种正常年龄结构或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中处于“社会化”阶段的人群减少,相应地,青少年“行为出轨”现象也将减少,有利社会稳定。三是,预示着人口规模缩减的时代即将到来,有利缓解人口压力。四是,还可促使老年就业以及老有所为及其“成功老龄化”(穆光宗,2002)的进一步实现,这对于一些老年人“实现老年价值”的追求以及减轻社会供养负担应都是好事。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目前我们的国家如前所言“既养老又养小还要养少”的不正常状况也可望趋于正常。
从实践出发:从容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我认为,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一个从实践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考虑解决问题的态度取向问题。——其意是指,是从实际分析解决问题?还是从中国人口转变怎样、总和生育率如何、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标准框定的人口现象怎样思考解决问题?对此,我主张取前一种态度。不仅如此,“从实践出发”可作进一步理解。2003年,数学大家吴文俊先生在谈中西方数学的异同时说:我们学现代数学即西方数学,主要内容是“证明原理”;而中国古代数学根本不考虑定理不定理,主要内容是解方程,即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使我顿悟到,我们研究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应如此(我在前面已尝试做到了这一点),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否则,用理论去框现实去“证明原理”(恕我直言,依我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研究基本上是在作“证明原理”即在证明按标准如何老化得不得了的工作),得出的结论只会把我们引入迷途,进而使我们解决问题的努力“南其辕而北其辙”。因此,求证原理脱离实践进展的研究法应改为解方程研究法,窃以为。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前沉重的就业压力、解困压力和社会保障压力,以及“既 养老又养小还要养少”的残酷社会现实,这些都说明“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2000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语),即人口过多仍是主要矛盾。鉴于此,笔者认为还是要抓主要矛盾破解问题,不能头发胡子并重抓或主次矛盾颠倒抓。值此笔者建言,我国当前尚不宜走“调松生育政策使人口年轻一些”之路。什么时候可调松生育政策?我以为这应在中国人口长远目标确立后(譬若7-10亿为好),视情况而定;而不能在长远人口目标未定的情况下,中途凭理论凭“本本”乱建议(如说把总和生育率调至更替水平)。到此,我呼吁全社会调整心态面对“卡夫丁峡谷”,从中寻求化解之策以求通过:
其一,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消除“人造老化”现象和减少被供养人口的堆积。
其二,其中要注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才资源,让纯被养人口部分转变为自养人口或作贡献人口。
其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观要与时俱进,不能抱着“正三角金字塔年龄结构才是正常的”观念不放,本世纪也不要追求恢复到那样。到底如何办?应纳入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作整体考虑和定位(这个问题,当前国家组织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应加以解决)。